天津的曲艺活动最早约出现于清代前期 。 刊行于清乾隆四年(1739)的《津门杂事诗》, 其69首云:“生子何须拜塾师, 居奇只唱耍孩儿。”诗后有注:“津邑窭人子,每命习唱连厢词,一名耍孩儿。” 乾隆五十年(1785)蒋诗在其所著的《沽河杂咏》中说 :“卖菜翁呼春不老, 小班子唱耍孩儿。 此蔬只许津门食,此曲惟应沽水知。”可见打连厢这一曲种早已植根天津民间。
乾隆六十年(1795)于北京刊行的《霓裳续谱》俗曲总集,收入流传于京、津一带的曲调30种。嘉庆元年(1796),杨无怪撰《皇会论》中有“莲花落,不耐看”,“稍可是侯家后的拾不闲”等内容,也记载了这类曲艺品种。道光、咸丰年间,曲艺有发展,不仅曲种增多,还出现了一些曲艺名家,如著名相声艺人朱绍文(艺名“穷不怕”)等。
那时的曲艺,曾受到移民的影响。自清顺治年间(1644)以来,来自江南的移民,多喜欢“南腔”,嘉庆年间刊行于北京的俗曲集《白雪遗音》中就收录不少东南各省的小曲;来自河北、山西等地的移民,多喜欢“北调”,当时的《霓裳续谱》记下“北调”小曲600多支。 这说明天津的曲艺出现过“南腔”、“北调”兼容的局面。
清咸丰十年(1860)天津被迫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相继设立租界。这些现象,都对曲艺产生了影响。当时,外地的曲艺顺着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从河北、北京、山东以及江南地区传入天津,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天津特色的曲艺艺术。到清代晚期,天津的曲艺已有木板大鼓、梨花大鼓、北板大鼓、西河大鼓、平谷调、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杂耍场、书馆已有数十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的《津门记略》,记载了小广寒、晴云馆、天复茶园、宝乐茶园、海耀茶园、丹桂茶园等当时彰明较著的几个演出曲艺的场所。
辛亥革命(1911)以后,社会教育受到重视,直隶教育会、直隶省学务会议分别于1913年9月7日和1916年4月9日公决:“改良鼓词”。1913年,天津成立了艺曲改良社,编唱新词,审订曲目,改编旧词。同年社会教育办事处还办起了盲生词曲传习所,培训盲艺人,传授新曲目,提倡科学和民主,创作了大量新唱词,供艺曲改良社社员与盲生学习演唱。这期间,唱片制作技术和留声机传入中国,许多外国大唱片公司(如“百代”、“高亭”、“胜利”等)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大量灌制戏剧、曲艺唱片。天津的曲艺名家如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金万昌、乔清秀、刘文斌、小蘑菇(常宝堃)等都录音灌制了唱片。这不仅使名家名唱得以保留和流传,也使广大听众能够在家中欣赏曲艺。
到1925年,天津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超百万。工业的腾飞,人口的剧增,促进了通俗文艺(包括曲艺)演出的繁荣。“三不管”(指日租界不管,法租界不管,中国政府也不管的南市一带),鸟市、谦德庄、地道外、六合市场、新大路等地聚集了大批撂地艺人。杂耍馆、书馆遍布全市。以后,天津的繁荣中心逐渐移至南市一带,杂耍馆、书馆见于记载的就有20多家。演出的繁荣又促进了曲艺艺术的发展。 京韵大鼓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 成为影响最大的曲种; 滑稽大鼓(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流)传到天津。继西河大鼓的几个支系(北口、小北口、南口及木板西河调)流入天津之后,朱(化麟)派、王(振元)派、李(德全)派等西河大鼓的几个主要流派都进入天津。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积累、移植,长篇书目已有50多部。
此时,相声艺人也汇聚津门,时调有长足发展,单弦荣(剑尘)派、常(澍田)派流入天津,联珠快书、铁片大鼓、平谷调、梨花大鼓、三弦弹戏、莲花落、双簧、荡调、弦子书、滩黄、辽宁大鼓、卫子弟书等曲种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天津战乱频仍,大批军阀、官僚、遗老及各类富户迁入英、法、日、意等租界,大量财富随着他们一同流入,促进了租界的繁华。30年代,法、日租界已发展为天津的中心商业区。尤其是法租界的劝业商场一带,已成为天津市的购物中心和游乐中心。
在以上背景下,天津的曲艺也发展到高峰时期,一些新型杂耍馆出现了,如位于泰康商场的歌舞楼(1934年改名小梨园)、天祥市场的新世界(30年代中期改名小广寒)、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的中原游艺场、劝业商场的天会轩等等。它们设施较好,所付包银较多,所约艺人多是第一流的,上演的节目大多比较文明典雅,代表了当时天津曲艺的最高水平。
30年代初,社会比较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城市近代化加快,劳动时间较前缩短,人们有了更多的消闲时间与消闲费用。大批男性市民为消磨闲暇时间,涌入游艺场所。杂耍低廉的票价,灵活的演出方式,对他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据《天津游览志》统计,华界著名的书馆就有22家
 |
| 图2-1 谢芮芝表演单弦 |
。电影院也纷纷加演曲艺。 南市一带的曲艺演出 ,常盛不衰。鸟市、谦德庄,地道外、三角地、新大路、北开等明地,热闹非凡。尤其是广播电台的出现,对曲艺的普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期间,河南坠子、山东琴书等曲种传入天津, 梅花大鼓、 辽宁大鼓、西河大鼓、天津时调、太平歌词、大雷拉戏、评书、相声都有长足发展,并涌现出一批创立新流派的代表人物,如花四宝、朱玺珍、王佩臣、马增芬、王兆麟、陈士和、张寿臣等。
与此同时,天津曲艺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技艺高超、风格鲜明的艺人,如:谢芮芝(单弦)、骆玉笙(京韵大鼓)、王艳芬(西河大鼓)、常连安(相声)等;还有一批起点高、条件好的新秀,如:常宝堃(相声),石慧儒(单弦),桑红林(京韵大鼓)、吉文贞(太平歌词)、花五宝(梅花大鼓)等。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一时间,天津的市面混乱,民心浮动,戏曲、杂耍等演出减少。到9月中旬,杂耍演出逐渐恢复以往的局面,其后一度表现为畸形的“繁荣”。
1942年下半年以后,天津的曲艺开始由盛而衰的历程。杂耍与戏剧合演成了绝大多数杂耍馆的主要营业方式。这期间,在艺术上有所发展的曲种只有相声、京韵大鼓和单弦。相声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小蘑菇(常宝堃)以及戴少甫、侯宝林的崛起;小彩舞(骆玉笙)在弦师韩永禄、刘文有的协助下,以刘(宝全)派京韵大鼓为基础,初步形成自己的流派特色:石慧儒在学习荣(剑尘)派单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嗓音宽厚、圆亮的特点,将荣腔女声化,进而形成自己沉稳中见巧俏、质朴中见华丽的唱腔风格。此外,还有一批新秀涌现在曲艺舞台上,如花小宝(梅花大鼓)、 王毓宝(时调)、 石连城(单弦)、武艳芳(河南坠子)、马三立(相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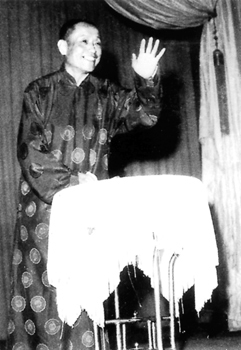 |
| 图2-2 相声演员常连安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将天津作为华北反共基地,致使天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当时,物价飞涨,人心不稳,社会秩序混乱,人们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各杂耍馆的上座率普遍下降。到1948年下半年,情况有所好转,观众也只有往常的十分之七八。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同全市人民一样,广大曲艺艺人欢欣鼓舞。1月20日(春节),有40多名艺人应邀到新华广播电台演播节目。从21日起,大小演出场所陆续恢复演出。 2月初 , 为庆祝天津解放,很多杂耍艺人于圣安娜歌厅举行了相声、大鼓、杂技、魔术、歌曲联合游艺大会。军管会文艺处于1949年6月份起举办剧艺工作者学习班,提倡编演新节目。曲艺艺人焕发了积极性,踊跃参加学习, 探讨艺术改革,同时还成立了“大众曲艺社”,努力创作和上演新曲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艺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演出活动。 当时仍取“什样杂耍”组织方式,演出的是曲艺(相声、京韵大鼓、山东快书、单弦、 梅花大鼓、 河南坠子等)和魔术、杂技的优秀节目。下半年建立了“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
1951年3月,中央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前线。 天津的曲艺演员常宝堃(小蘑菇) 、 赵佩茹、程树棠、郭少泉参加首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在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进行慰问演出 。 在完成慰问演出任务后于4月23日归国途中遭美帝战机扫射,常宝堃、程树棠光荣牺牲,赵佩茹,郭少泉等受伤。美帝的行径激起天津市人民的无比愤慨。为悼念两位烈士,天津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中央慰问团及天津市党政领导、各界知名人士和文艺界共15000多人参加送葬仪式 , 3万多市民参加祭悼 。 烈士的牺牲和盛大的祭悼活动,教育和激励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促使他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同年12月,按照烈士的遗愿成立了天津曲艺工作团。自此 , 曲艺艺人更加积极地配合党的各项中心任务开展宣传,积极创作、演出新曲目。天津曲艺工作团创作演出的宣传 《婚姻法》的曲艺剧 《新事新办》,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获创作三等奖、音乐一等奖。与此同时,许多曲艺演员积极申请赴朝,马三立、李润杰、骆玉笙、石慧儒、常宝华、苏文茂等先后参加第二、三届赴朝慰问团,到前线进行慰问演出。1953年,天津曲艺工作团改建为国办团体,加强了领导班子和演员阵容,也充实了创作力量。
这个时期,天津曲艺界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狠抓创作,不断演出新曲目;同时挖掘传统曲种,整理传统书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曲艺进行不断的改革。1954年,率先记录、整理、出版了著名老艺人陈士和的评书《聊斋》。1956年,记录、整理、出版了著名老艺人张寿臣的单口相声;挖掘、排演了濒于失传的荡调、马头调以及属于“时调”的各种小调;整理、改编了《论捧逗》、《批三国》等传统相声;对不少传统评书、鼓书进行了剔除糟粕、保存精华的改造。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津观看京韵大鼓专场演出,对搜集、整理京韵大鼓传统曲目的问题作了指示。同年3月举办了天津市著名曲艺演员优秀节目联合演出,共演出6个专场44个节目,其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曲目占二分之一。随着新曲目的不断涌现, 《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苦菜花》、《红旗谱》等反映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均被改编成长篇评书、鼓书上演。这期间,市曲艺研究室同演员合作,搜集、整理了京韵大鼓传统唱词一百多段,并将一些唱段搬上了舞台。同时停演了不少黄色或反动的曲目。李润杰以数来宝为基础,将山东快书、相声、评书熔为一炉,创造了“快板书”。工人业余演员王家骏将天津时调“大数子”发展成为脍炙人口的“天津快板”。天津时调“靠山调”变化了衬腔,京韵大鼓创造出了散板板式,梅花大鼓摸索出了新的板式,石慧儒改革了岔曲唱法,工人业余演员董湘昆规范了京东大鼓的板眼。
同时期,解放前成名的不少老艺人宝刀不老;中年艺人风华正茂;一批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享誉曲坛,如常宝霆、张伯扬、苏文茂、刘文亨、高英培等。山东柳琴、湖北渔鼓等曲种此时由业余演员带进了天津。
“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的曲艺受到摧残。从1966年6月开始,天津市曲艺团和各区曲艺团、队陆续停止演出。随后, 各区的曲艺团、队均被解散。著名演员大多被批斗,绝大多数演员包括马三立、 苏文茂等被下放到工厂、 农村劳动;从业人员大批裁减转业到工厂或企业单位。1968年12月,天津市曲艺团一度与天津市杂技团合并,改名“天津市曲艺杂技团”。书场茶社全部被改作他用;演出曲艺的剧场、曲艺厅停止了正常的营业;很多挖掘、整理的成果被付之一炬。天津曲艺跌入了低谷。但是群众业余曲艺创作、演出活动仍比较活跃。虽然演出内容多为公式化、概念化一类的说教之作,但它保存了一些曲种的火种,京东大鼓还扩大了观众群,在较大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对口词、讲故事等曲艺形式风行一时。天津市曲艺杂技团与后来的天津市曲艺团均高举“宣传”的旗帜,艰难地维持着曲艺这块民族民间艺术阵地 , 创作演出了相声 《挖宝》、天津时调《军民鱼水情》等较好作品,并先后招收两批学员,由骆玉笙等任教。在严酷的环境中,天津曲艺界顽强地挣扎着,一些曲种还有所发展。在业余舞台上,山东柳琴的演唱技巧被丰富了,出现了京韵大鼓表演唱和由女演员表演的对口山东快书。
1976年10月“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粉碎后, 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 天津的曲艺恢复了生机。随着党的政策的逐步落实,“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冲击、排斥的曲艺名家和曲艺演员重新回到曲艺队伍;于1979年12月,由原和平区、红桥区、南开区曲艺团,河西区、河东区书曲队,以及各区杂技团、队的大部分演员共同组成的天津实验曲艺杂技团建立;1981年9月1日,长虹曲艺厅开幕,它是天津实验曲艺杂技团的主要演出阵地;一些街道文化站和区文化馆也开始演出曲艺。
80年代以来,天津曲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在演出、创作、表演艺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加之各种汇演、调演、义演、专场演出、慰问演出不断,“津门曲荟”已举办九届,活跃了曲艺市场。另外,还于1981年承办了全国(北方片)曲艺观摩演出,1991年承办了首届中国曲艺节。这期间出现的长寿园、燕乐、名流、中华等茶园成为天津曲艺的主要演出阵地。曲艺作家群体的实力增强,何迟、王允平、朱学颖、张剑平、王济、夏之冰、杜放等笔耕不辍;王鸣录、杨志刚等悄然崛起。同时,涌现出两个优秀的表演群体。一个是由中年演员所组成,有刘春爱(京韵大鼓)、马志明(相声)、姚雪芬(铁片大鼓)、张雅琴(梅花大鼓)、张志宽(快板书), 以及弦师张子修、 韩宝利等;另一个是由70年代的学员所组成,主要有籍薇(梅花大鼓)、刘秀梅(单弦)、高辉(天津时调)、郝秀洁与杨雅琴(西河大鼓),以及弦师王力扬等。此外,还涌现出王莉、张楷、王哲、宋丹红、陈宝萍等一批新秀。这些青年演员大多毕业于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与此同时,曲艺理论研究取得成果,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天津时调、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和相声等曲种,在艺术上又有创新,特别是骆派京韵大鼓有新发展。骆玉笙的演唱,增添了苍劲的气势,韵味愈发醇厚, 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 风靡全国。群众业余曲艺创作、演出也十分活跃,武乡琴书、常德丝弦等相继出现在天津业余曲艺舞台上。天津市曲艺团在管理上进行了改革,为曲艺事业的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积累了经验。在几次全国性的创作评奖中,天津都有作品参加。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曲艺节目评奖、1981年全国(北方片)曲艺观摩演出、1984年全国相声评比、1986年全国曲艺新曲(书)目比赛、1990年“长治杯”全国曲艺(鼓曲部分)大奖赛、1995年首届侯宝林金像奖电视相声大赛、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天津都获得了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