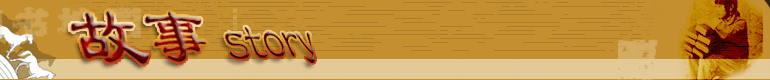|
华世奎的故事 张达骧家与华氏是累代世交,并有姻联,达骧从10岁以来,在自己家和亲友宅第应酬场合上,常常见到此老。刘炎臣从1928年以后几年间,参加严范孙、林墨青等创办的国文观摩社,每周作文一次,华氏是被邀请评阅试卷的老师之一,与华氏有师生之谊。我们两人对其言论风采,以及出处行事,略有所知。兹就回忆所及,拉杂写出,以供参考。
一、生平黄金时代
华世奎的父亲,名承彦,字屏周,乡人称之为“老华五爷”,在家经营盐务,未出仕,性极爱好书画。往年张达骧在华家曾见到有署名屏周上款的团扇、摺扇数十柄,其中包括当时的名公钜卿如李鸿章、李鸿藻、翁同和、翁曾源、潘祖荫、孙毓汶和张达骧祖父张之万等人的作品,可见华承彦虽未曾出仕,而其交游却是很广的。
华世奎为华承彦的独生子,字启臣,号壁臣,晚年自署“北海逸民”。生于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颇为乃父所钟爱,期之非常殷切,自幼督教很严,应对进退,全有矩度,故华世奎成就极早,一生学行,得力于家教为多。
1879年(光绪五年)华世奎16岁时入泮,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科拔贡,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章京(办事——满语),在军机处当差。1893年(光绪十九年),应癸已顺天乡试,考中举人,仍在军机处任章京。因擅长文移,办事得体,被提升为“答拉密”(满语领班之意)。这个“答拉密”职务,在清廷官场,多称之为“军机领班”,众呼“小军机”,但与领班的军机大臣,不可同日而语。清季军机处大臣中,年老不胜繁钜者为多,庶政势不能不倚重“答拉密”襄赞一切。京内各部、京外各省,遇有必须军机大臣题奏的事件,往往要恳托“答拉密”为之向各军机大臣陈明,统一意见。在军机处方面,全体军机大臣,如对各省督抚有什么指示机宜的官信,多由“答拉密”秉承各军机大臣的意见启稿书写。这项官信,都带天、地、元、黄若干号的字样,其内容乃是追补廷赍未竟之意,但有时也有廷赍所不便明言的内容,故用私人名义交换意见,当时通称这种信件为“内阁官信”。还有,各省道府州县各官的升迁调补,当事人为达个人目的,全要想方设法找门路向“答拉密”提出请求,“答拉密”根据情况,为之安排。不言而喻,“答拉密”这个差事虽小,在军机处内却可左右一切,自然地就能够收到文官自富的好处。华世奎精于翰墨,少年有为,故在他官居“答拉密”的年代,得心应手,深为各军机大臣所喜。
1911年(宣统三年)朝廷内阁改制,以庆亲王亦勖为首的亲贵内阁成立,在内阁设阁丞一员,华世奎由“答拉密”擢升为内阁阁丞。当时内阁协理大臣为徐世昌,徐是华世奎的表侄,两人交情极深。这时二人互相表里,华世奎乃得以左右逢源,称心如意地放手办事,内阁中附设的各局,莫不听命于阁丞,为华的马首是瞻。
不久,武昌革命军兴,被罢黜的袁世凯,重行膺命入京补授内阁总理大臣,袁与华世奎本属多年共事相知的故人,对华更加倚重,并规定阁丞官级为正二品,遂使华的位望,居然副相矣。此时可以说是华世奎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二、书写退位诏书
当辛亥革命风云紧迫时,袁内阁取得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同意退位之后,即命华阁丞书写宣布退位诏书。华世奎写好清廷退位诏书,把它装成一幅横‘匾;备匾亭一座,由太监抬入太和殿,请摄政乏载沣亲自监临,以成此隆重典礼,诏信全国人民。但没想到摄政王到场之后,竟提出了异议,他声明个人并不同意皇帝退位,认为这项沼书可以不下,他频频地连声说:“我看算了吧!算了吧!”四顾左右见无人响应,就又连声说了两句:“可以不必了!可以不必了尸然后自行出殿去了。华世奎看到这种情形,认为退位是既定之事,绝无有因为王爷—时之言,推翻御前会议决定的道理,当即按照原定步骤,让人把摆设退位诏书的亭子,抬出天安门,宣布了清廷退位。
三、始终忠于清室
民国建立后,华世奎因怀念“故主”,意态消极,乃借省亲,退隐津门,以示“忠于先朝”,“不做贰臣”的夙志。当时北洋政府当权,深知其才,力谋挽回,—时征召的信使,往返于京津,百般劝解,终无成效。华世奎从此自号“北海逸民”,度其超然鸣高的生活。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李石曾在北京参予驱逐溥仪出宫之役。事后,华世奎对李石曾极表不满,见人辄骂李是“文正孽子”,“李氏罪人”。因李石曾名煜瀛,系李鸿藻之子,鸿藻谥文正,故华发此牢骚以泄愤。
1925年,溥仪出京来到天津,住在日租界张园,华世奎常去“恭请圣安”,以示念念不忘“旧君”。但是,华世奎对郑孝胥是表示不满的。1929年,华世奎曾说郑孝胥在张园诳去宝石价值数十万元,勾结西人,意图创办《万国诚报》。并说郑孝胥视“张园”(指溥仪)为奇货,不定哪
一天,“张园”会被他出卖的。表明华世奎时时不忘维护“旧主”权益。
民国成立后,中国男人都先后把脑后的“小辫”剪掉了,而华世奎却自居例外,仍把他的那个小辫当做宝贝看待,不愿剪掉,以表示他对清室的“忠贞”。辛亥革命后不几年,华世奎方隐居乡里,他曾很有感触地在自己早年留着小发辫的照片上写了《甲寅自题小照》诗两首。其一:“荏苒年华五十强,浑如一梦熟黄梁。本来面目存真我,就是儿时华七郎。”(华世奎行七,晚年乡人恭称“华七爷”)其二:“田园株守作闲人,文物衣冠付劫尘。惟此弁髦难割爱,留同彩服寿双亲。”由此可见,他不愿剪掉小辫的顽固心情。
民国初年,南皮县张氏立姑、春姑二女因被天津西头恶霸戴富有骗婚,意图转卖,姐妹双双服毒自杀。“双烈女”惨痛事件发生后,天津好事者,感于这“双烈女”的“贞节”,给她们姐俩出了一场大殡,并立纪念碑,一个是“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一个是“南皮县张氏双烈女庙碑”,全是华世奎“书丹”的。有趣的是“双烈女”自杀时是1916年,即民国五年,而华世奎在写年号时,避讳写“民国五年”,写的是“我皇清退位之五年”。
华世奎还反对学生们在做文时用新名词。1928年严范孙,林墨青在天津创办国文观摩社,华世奎被邀请为评阅试卷的老师之一。有一次他出的作文题是《四书》上的一句话“放利多怨说”。学生刘基汉(炎臣)在文中用了“需要”和“社会”等新名词,他在评卷时,认为不对头,在该生试卷顶眉上批写“‘需要’二字不入文”,又批写“‘社会’二字是新名词,入文终嫌不雅”。其头脑的顽固,可见一斑。
四、被称“中堂”趣事
因为华世奎曾任清末内阁阁丞,显赫一时,因此当他退居津门时,招出一段笑话。
当1926年,褚玉璞以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正盘踞天津。他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虚名,有时设宴招待所谓名流大老,吕海寰、严修、华世奎等多在被邀请之列。气次督署欢宴名流,吕海寰、华世奎应邀前往,当时褚玉璞对“华七爷”极尽推崇恭维之能事,让坐时称华为“中堂”,并言有“中堂”在,当然要请“中堂”坐首座。华世奎问道“谁是中堂?”接着说“有镜老(吕海寰宇镜宇)在,我不敢僭座。”结果让再让三,还是吕海寰坐了首座。席间,褚每向华接谈,必称“中堂”,华本人也未便再驳,其他在座各位,却莫不忍俊不禁。因此之故,华在知交中一时得了一个“华中堂”的诨号。按清代官场旧习,称大学士为中堂,而大学士又往往充任军机大臣。华在清末被称为军机领班,所以致有无知的褚玉璞误称华世奎为中堂的趣事。
五、发怪论说谐语
华世奎为人,虽极端保守,但颇以道义为重,在谈论人物时,常是怪论横生,且往往杂以诙谐,尽妙尽趣。如他在评述近代教育时曾谈过:“中国局面之坏,坏在两个人身上,前有张文襄(之洞),后有严范孙(修),把局面就弄糟了么!”因他不接受新事物,反对新教育,故发此怪论。实际说来,张乃华的老师,严乃华的亲家(华的长子泽宣为严的女婿)。华的信口而谈,无所规避如此。
1926年冬,清末尚书吕海寰病故天津,吕固为华世奎的挚友,华挽吕联云:“闭户闲居,多看几出文明新戏:趋朝行在,又少一个忠荩老臣。”因为当时吕海寰的女儿孟阁,以故为其丈夫盛宣怀之子盛聘臣所黜,正在丑声四播,华世奎遂以闭户看新戏之词以嘲之。
伪满洲国成立时,有人以华世奎为忠于清室的遗臣,特劝他向溥仪上贺表,他未为敌伪所诱,并出以谐语说,“掌柜的是旧人,字号改矣,可以不去。”闻者怃然而退。
1937年“七七”事变时,有人拟请华世奎出头维持天津的临时治安,他仍是未为所动,并说:“吾老矣,不能用矣。”以此却之。并私语人说:“风烛残年,蜡头无几,何必添彩。”其语言之有风趣又如此。
华世奎平生交友笃挚,坚刚有至性。他曾对人谈及,海内有最知己的朋友三人:—为嘉善的钱能训(干臣),一为宁洲的朱家宝(经田),另一人为肖县的段书云(少沧)。
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时,拟请华世奎为助,华因供职军机处,不能兼顾谢之,为之转荐钱能训。徐委钱为左参议,后来钱任国务总理,与华为生死之交。朱家宝任平乡知县时,正值庚子年义和团之役,他主剿不主抚,平乡境内竟肃然无事。不数年,累迁吉林巡抚,调安徽巡抚,民元后又为直隶民政长官,与华相爱如手足。段书云曾为清河道,为华的畏友。1923年到1924年之间,钱、朱、段三人相继故去,华世奎哀挽至痛,有过人之情。
六、华氏晚境
华世奎一生只于清末供职军机处,辛亥革命后,即未再出任,退居乡里,除参加友朋诗文酒会酬酢外,以鬻书自娱,自署“北海逸民”,过其安贫乐道生活。华世奎是近代天津书法名家,所写颜体字,功力极深,大自寻丈,小至蝇头,端楷正书,苍劲挺拔。使人感到大不散漫,而小不逼侧,坚刚之气,指挥如意。他生平为人写了许多牌匾和碑记、墓志铭等,在三津留下了不少可资纪念的文物。
华世奎著有《思暗诗集》,是其自咏和与友朋唱和之作,多抒怀明志,曾自端书印行,为其名贵之作。他谈到作诗,曾慨乎论及“穷不必工”和“不穷必不工”的见解。他说:“昔人云,诗必穷而后工。今余所处之境,穷之极矣,诗犹不工何也。可见文字美劣,仍视其学问,阅历何如。倘谓穷则必工,则乞儿人人李杜矣。虽然,穷不必工,不穷必不工。坐拥高赀,日奔走乎势利之场,摇笔即作牢骚之语,以冀掩其酒肉鄙俗之气,则是披孟尝之裘,而吹伍员之箫,吾未见其成声也。古人之言,岂欺我哉。”言为心声,从华氏之论诗文,足以窥见他的衷曲,而峻伟端炼,正与其书法同肖其为人。
华世奎作为名书法家,订有“笔单”,往年天津各南纸局多代收书件。每逢岁杪,兼润书扇,以所得润笔,资助贫寒。但多为其门人代笔,扇头必印小章“小直沽人”,因天津旧称“小直沽”,作为暗记,即凡印此小章者,皆属赝品。所写的擘巢大字,也有是别人代书的。他在1926年所写的日记自序里谈到:“人生遭际,变化无方。余生平碌碌无所长,惟遇事敢作,不畏难而阻,有所见敢言,不因势而诎。”又谈到:“……四十以前,由中书升入军机,累迁至阁丞,时未十年,侧身卿贰,何其易也。迨五十以后,双亲见背,家事丛集一身,日处忧惶枯灼之中,求片刻宽舒,而不可得,又何其难也。”这是他自述在宦海得意与退隐后为家务所困扰的大概情况。华世奎家本素丰,只因好义轻财,不善经营,致晚年卖字自给,时处困境,曾赋有《感怀》诗:“困守寒毡十七年,当年悔否饮廉泉。春衣典尽余尘桁,破砚磨穿亦石田。独恨此身穷不死,尽多同病苦谁怜。觉来又是晨炊近,检点囊中无一钱。”晚年一贫至此,但犹不时资助友朋。
华世奎于1942年春夏之交,故于天津里第。伪满“赐谥贞节”,其后人曾印出《华贞节公诗存》一本,内容乃华生前工楷手书的诗稿。
华世奎生前曾说过:“人死如烟,身后事,死者不负责。”所以他在临终时,未留遗言。终年七十有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