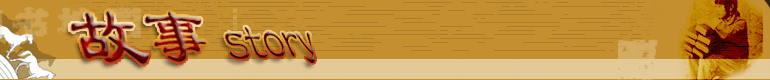忆曹禺先生二三事
天津是曹禺的故乡,在南开中学学习时曹禺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1926年9月万家宝首次使用“曹禺”这个笔名,在天津《庸报》上发表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揭开了他卓越创作生涯的序幕。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也是由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于1935年8月首次在国内公演的。
1985年由我主持筹建天津戏剧博物馆的工作。当时我们热情地邀请曹禺先生担任天津戏剧博物馆的名誉馆长,他在晚年不顾年高体弱,欣然接受了这个荣誉职务,并亲自指导着天津的戏剧事业的发展,其热爱乡土之情,何其眷眷,何其殷殷,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这层关系,我与曹禺老师的交往就多了起来,常请求曹禺老师在建馆工作及戏剧研究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对于我的这两项要求,曹禺和李玉茹老师都欣然应允,使我非常感动。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曹禺先生那平易近人、热心可亲的音容笑貌,现在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面前。
曹禺先生是个情感丰富且十分怀旧的人,这点在我与先生的日常接触中也能感觉到。作为曹禺先生的学生,我常常去北京医院探望他,有时向先生汇报工作,请教学业。我发现他在医院写字蘸墨时所用的是一个破旧的铜制的小方墨盒。于是,一天我买来一套高级蓝花笔洗、笔筒、印泥盒和新的圆铜墨盒送给先生,并斗胆向先生索要那个旧墨盒,由天津戏剧博物馆收藏。先生笑着讲:“我还没死呢......”回绝了我,并且手扶着旧墨盒。望着他那认真而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猜想先生或许想起了美好的过去。他或许想起养育过他让他既怀恋又憎恶的公馆故居——万公馆;想起他读书学习呆过的书房,还有那只与他做伴的叫“来福”的小狗......最后他还是情愿地将他使用过的毛笔等用具捐给了天津戏剧博物馆。曹禺先生对哺育过他、并给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天津、南开,总是怀着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
从那以后我与曹禺先生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我常去他家做客,汇报工作,在戏剧研究上也得到他关切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由于这层关系,1996年年初,我和同窗好友冯景元、张涛、马庆山、梁吉生诸位先生一同创作编写了8集电视剧《张伯苓》。在讨论谁题片名最好时,大家研究后一致推举我专程去北京请曹禺先生为这部电视剧题写片名。之所以请曹禺先生题写片名,还因为电视剧《张伯苓》的主人公张伯苓是曹禺先生在南开学校就读时期的老校长,也是曹禺先生走上戏剧之路的领路人之一。
曹禺先生患病卧床多年,近来身体欠佳,虽然我是先生的学生,但还是不忍心去打扰他老人家,可一想起众人的嘱托,就又鼓起了勇气。1996年夏,前往北京医院。
根据曹禺先生当时的病情,医院不准任何亲友探视,更谢绝客人来访,但听说我是先生家乡的客人,医院破例同意探视。以前探望先生时,进他的房间不用换鞋,但这次根据要求必须换上拖鞋才能进病房。我想先生的病情肯定加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打扰先生,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和不安。走进曹禺先生住了八年的病房,李玉茹老师热情地迎接了我,她快步走到先生的床边,在先生的耳边高声说:“天津的殿祺同志来看你了。”曹禺先生正打吊针,此时他睁开眼点点头,露出了微笑,用右手向我打招呼。我把水果和食品交给长期护理先生的护理员小白,随着走进先生的床边向他问好,并握住他的手。他的手背因为长期打针输液,被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看了叫人心疼。可想而知近
90岁的老人用多大的毅力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呀……曹禺先生慢声地问我:“殿祺,有什么事吗?”李玉茹老师随声对我说:“要做什么快给曹禺老师说。”我马上回答:“我们正在搞描写您的老校长张伯苓的电视剧,此次专程来京请您为电视剧题写片名。”这时他睁大了眼睛高兴地说:“好!好!”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说过几天写好后给我寄到天津。
回津后,过了几天,当我打电话与北京联系时候,曹禺先生的护理员小白回答:“已经写好了,曹禺夫人说给您寄去。”我怕丢失,就让对方先别寄,转天亲自去取。第二天我就到了北京医院,等候取走曹禺先生的题字。可真没想到小白怎么也找不到曹禺先生为电视剧《张伯苓》题写的片名了。这时李玉茹老师很着急,不好意思叫我久等,就让我上楼来。上楼时正看到李玉茹老师很着急的样子批评小白。正在大家为此事着急而又没有办法时,曹禺先生躺着轻声说:“别找了,也别着急了,你们扶我起来,我再重新写一幅。”这下可解了围。
玉茹老师她很担心先生的身体,同样我也是如此。可以看出李玉茹老师不愿打扰曹禺老师养病。这时,又偏偏出现了这个事。我非常理解她的心绪。玉茹老师是非常爱曹禺的,她不愿老师的病情有一点加重。因为曹禺老师被病魔缠绕了整整八年了,李玉茹老师也伺候了他八年。她护理曹老时完全遵照医生嘱咐,所以特别严格。记得玉茹老师是很爱吸烟的,由于她精心爱护曹禺的身体,保持病房中的清新空气,她努力克制自己的烟瘾,没见过她在室内吸过一点烟。有一次,看望过曹禺老师后,我先告别离开病房,随后玉茹老师也从医院出来,她在去东单邮局寄信的路上很快点着一根香烟,深深地吸着烟卷,又从口中厚厚地吐出团团的烟雾。原来焦虑、担心、奔忙、赶赶落落,计算着时间过活的玉茹老师,这时仿佛才松了一口气。她快步走着,为的是等寄完信,马上回到病房好服侍治病的曹禺先生。微风吹拂着她那很少修整的花白的头发,与烟云飘动着。
玉茹老师看到曹禺先生已表态,不好意思再婉言谢绝了。于是小白和我一同扶曹禺先生从床上坐起、下地,搀着他走到桌前,老师慢慢地坐好。我俩又抬着椅子将老师往前再靠近桌子。我们迅速地将笔墨纸砚摆好,曹禺先生拿起毛笔,慢慢地蘸墨,从容地在宣纸上竖着写下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张伯苓”,并在落款处写上“学生曹禺”四个小字,以示对老校长的敬仰之情。这位86岁高龄而又功成名就的长者,他那种谦虚、尊师的品德值得我辈学习。题字之后,我们扶着老人缓缓地坐在沙发上准备吃饭。这时写好字的宣纸墨迹已干,我轻轻地卷起来,仔细收好。令人感动的是,两位老师一字不提酬金的事。
作为艺术家,曹禺先生在艺术上执著的追求,对自己的要求到了苛求的地步,但在生活中,他是个随意而宽容的父亲、师长、领导,他的许多品格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下一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