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津版《白毛女》重现经典魅力
紫 茵 |
|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天津版”经典民族歌剧《白毛女》以新面貌、新风采呈现舞台。清脆的开场铃声响过,一群老乡打扮的男女,叮叮咚咚大步登台,摆出阵势、拉开架势:“七十年前延河旁,搭台演戏哭恓惶。唱的就是《白毛女》,哭得咱是泪汪汪……”原来,这就是导演李稻川新添的个性创意、神来之笔, 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华阴老腔”的黄土之声, 一下将观众带入了《白毛女》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 《白毛女》剧作诞生的那片土地。高亢激越的弦歌锣鼓,粗犷豪放的嘶声呐喊, 天然散发出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
大幕开启,音乐奏响。听到的是民族乐队的“原声”原味,看到的是北方山野的“原貌”原形。一种七十年前的历史质感油然而生, 一种七十年前的淳朴之风扑面而来。 原来,这还是导演李稻川坚守的艺术理想、真诚表现。由“讲话”精神催生萌芽、开花结果的民族歌剧开篇之作,深深植根于黄土文化。这朵奇葩带着泥土芬芳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仍保持者蓬勃鲜活的艺术生命力。但舞台上的《白毛女》,因太多太厚重的交响化音响、太多太花哨的现代化舞美, 开始渐渐散失原本的神形风貌、品性魂魄。“天津版”的精神回归与观念超越, 这种声音、这幅画面的舞台呈现,实在已经久违了。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十七岁的少女喜儿出场了,她就站在黄土高坡上,红袄、青裤,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垂在胸前。清甜圆润的女高音唱出这首家喻户晓的名曲。李瑛无愧于天津歌舞剧院头牌女角荣誉,以深厚的实力、功力和丰富的经验、真情,仿佛喜儿灵性附体一般,自自然然、真真实实地唱,真真实实、自自然然地演,演活了一个足以引人怜爱、同情的悲剧人物。总体上,喜儿比金子表演状态更加自然松弛。最难能可贵的是,李瑛并未因自身年龄与角色年龄的差距而产生负面心理,更未在声音造型和表情姿态上特意、故意、刻意地“装嫩”“发嗲”“卖萌”“假天真”“扮少女”,她让观众越来越相信她就是河北佃农杨白劳的“心头肉”,她就是那个美丽青春惨遭不幸被损害糟蹋的少女。喜儿送大春出门的那一刻,恋恋不舍、羞羞答答,李瑛的一侧身、一低头,楚楚动人、毫不夸张;喜儿和黄母见面的那一刻,惊恐不安、颤颤巍巍,李瑛的一斜肩、一扭头,悲悲切切、绝不做作;喜儿被东家污辱的那一刻,悲愤难当、痛苦欲绝,李瑛的一垂手、一仰头,凄凄惶惶、情不自禁……所有的唱段都从人物内心出发,依据可靠、走向清晰。最出彩的咏叹应该是第四幕的《恨似高山仇似海》,她的嗓音焕发出经历“深山苦度,煎熬三四年”后的沧桑感,使白毛女的艺术形象更加丰满动人。
曾经听过多版男中音演唱的“十里风雪一片白”“廊檐下红灯照花了眼”“喜儿喜儿你睡着了”“老天杀人不眨眼”等杨白劳的经典唱段。“天津版”男一号一出场,不由让人为之一振,好像用的是男高音?虽似不如听觉记忆中那般粗壮厚实,却别有一种柔婉、含蓄、细腻的美感。突然发现张成喜真是好演员,嗓音那样漂亮华彩,同时他的戏可是下足了功夫——女儿身边慈祥的父亲,财主面前抗争的佃农,乡亲眼里憨实的老汉,张成喜塑造的这个人物非常准确到位,且表演浑然天成,几无雕琢印痕。这是笔者看到歌剧角色中最符合人物感觉的杨白劳,最像杨白劳的杨白劳!这个杨白劳,应该成为中国歌剧舞台一个具有示范作用的艺术形象。
笔者在现场欣喜地看到,相当比例的非音乐界人士和普通市民被民族歌剧经典的独特魅力所吸引、所折服、所倾倒。演出过程秩序井然:中场休息无人提前离去,全剧结束反映热烈,掌声持久;最后散场时,观众仍旧兴致盎然、津津乐道。看来,他们都是真心喜欢《白毛女》,喜欢舞台上的演员,还有乐池里的指挥和乐师。有位专家认为,这不是简单随意、应景式地复制经典,而是自觉自为、创新性地传承经典。经典,因此而获得新的生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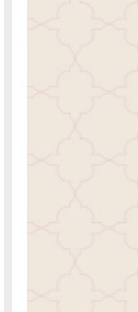 |
|
 |
|
|